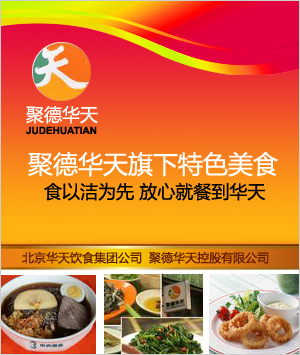少数民族服饰的文化内涵 (2)
时间:2010-03-03 13:59 长沙旅游网 点击:次 我要评论()
可见,衣裳的制作是人类社会进步即文化的产物,服饰本身即是一定社会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前人,对服饰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视
可见,衣裳的制作是人类社会进步即文化的产物,服饰本身即是一定社会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前人,对服饰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视,甚至将其提到天下治乱的高度来认识。《易.系辞》就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服饰,竟然成了治理天下的工具。在中国历史上, 确曾这样做过。“五百里甸服,五百里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正是以衣分界而治理的形象写照。而在同一治内,衣饰则成为赏罚的手段:“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和矜孤,取舍好让者,命于其君,然后得乘饰车、骈马,衣文锦。未有命者,不得衣裳,不得乘。乘衣者有罚。......未命为士者,不得乘饰车朱轩,不得衣裳。庶人单马 木车,衣布帛。”1、就是到了近现代,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地方和民族中,这样以衣饰标志等级或赏罚的做法仍然存在。
我们知道,人类在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文化,可以区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和制度文化这样三种大的类型。其中,物质文化实在具体,具有形象,直观的特点,和人们的生产生活关系十分密切,因而处处使人们觉得不可缺少。马林诺夫斯基指出:“人的物质设备:举凡器物,房屋,船只,工具,以及武器,都是文化中最易明白,最易捉摸的一方面。它们决定了文化的水准,它们决定了工作的效率。在一切关于民族‘优劣’的争执中,最后的断语就在武器,它是最后的一着。在一个博物院中的学者,或在一个喜讲‘进步’的政客心目中,物质文化是最先被注意的。”
和一切物质文化的创造物相一致,服饰也拥有具体形象、直观显眼、实用普及等特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都必须穿戴一定的服饰,而且他的服饰是无保留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人们只要上下打量一眼就可以了解到他的服饰的质料、形制、色彩、组合,从而也就可以大略了解这个人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水平之上。由于服饰可以由各种各样的材料剪裁缝制而成,衣裙的用料如何,也就可以反映出穿衣人自己及其生活的社会的生产发展程度,反映出穿衣人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又由于服饰都不是纯粹的天然物,总要进行剪裁缝制、琢磨加工和连缀搭配,所以它又直观地反映出一定地区、一定民族乃至一定时代的工艺技术水平。如前所述,服饰还是一定社会内地域划分、等级区别的标志,一个人的服饰也就是一定社会地位的显性表现。除此而外,人们的服饰还都是工艺品、艺术品。它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又必须与具体的人体结合而充分展示其艺术性,因此它既供穿戴者欣赏,更供旁观者欣 赏;同时,服饰这一艺术品不依告与日常生活的分离而恰恰要依靠与日常生活的统一而确立自己的艺术地位。这样一来,服饰的质料、形制、款式、色彩无不体现出穿着者本人和周围人们的审美情趣、审美习惯、审美追求和审美理想,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甚至体现出一定的礼乐制度。
(责任编辑:admin)
收藏到书签: